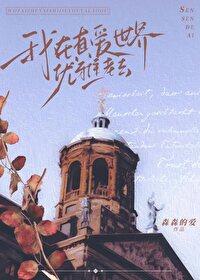书籍简介
首章试读
“原、原来,全身疼得仿佛被汽车车轮反复碾压过是、是这种生不如死的感觉” 乍一苏醒过来,周身的剧痛让重伤者先是无意识地在灵魂和肉身之间设下了一道无形屏障来隔离感知,随即,她的脑海中莫名浮现出了这样一句感慨。 之所以说是“莫名浮现”,是因为此刻为数不多的清醒意识令重伤者猛然反应过来,其实“自己”之前完全没有听谁讲过这样的形容比喻。 “既然如此,我怎么会产生这种恍然感觉” 虽然身体此时依旧处于昏迷不醒的状态,但更多更具体的念头自重伤者的脑海深处逐一浮现出来 “还有,我是谁来着哦,我记起来了,我是我是梅,是了,我是梅韦兰不,不对我应该是梅阿切尔夫人是的,我已经结婚了,不久前嫁给了纽兰阿切尔” 不过,重伤者并没有因为记起自己的身份而感到轻松,反而有些怅然若失,甚至觉得丝丝违和。 与此同时,她心底忽而灵光一闪,又察觉到了另外的不妥之处,不禁就着先前的那个疑惑迷迷糊糊地琢磨起来 “对了,被汽车车轮碾压汽车为什么我联想到的不是马车或者火车呢汽车明明我的生活中到处都是马车啊,而且,刚刚撞到我的,就是一辆便捷的布朗马车” “夫人夫人哦,上帝啊,请您保佑保佑可怜的夫人吧,她是” 一阵似远又近的急切呼喊声断断续续传入重伤者的耳畔,又似乎有不少人在靠近自己的身边,熟悉的,陌生的,随之而来的又是一阵阵惊恐的抽泣声和悲悯低沉的呢喃祈祷 周围的混乱嘈杂声越来越大,重伤者虚弱得连眼睛都睁不开,却不曾被打断思路。 “好像、好像我其实更熟悉那个叫做汽车的交通工具可明明咦我似乎、似乎根本不是梅,而是而是谁来呢奇怪,为什么我会认为” 不等双目紧闭的重伤者彻底分析清楚到底哪里奇怪,在她此时感应不到的地方,她的灵魂与这具身体间的那一层无形保护屏障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这一刹那,一阵又一阵铺天盖地的剧痛之感如山呼海啸般重新席卷而来,瞬间冲散了重伤者心底升起的那一抹警觉探究。 “嘶太太太疼了太、太疼了疼疼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