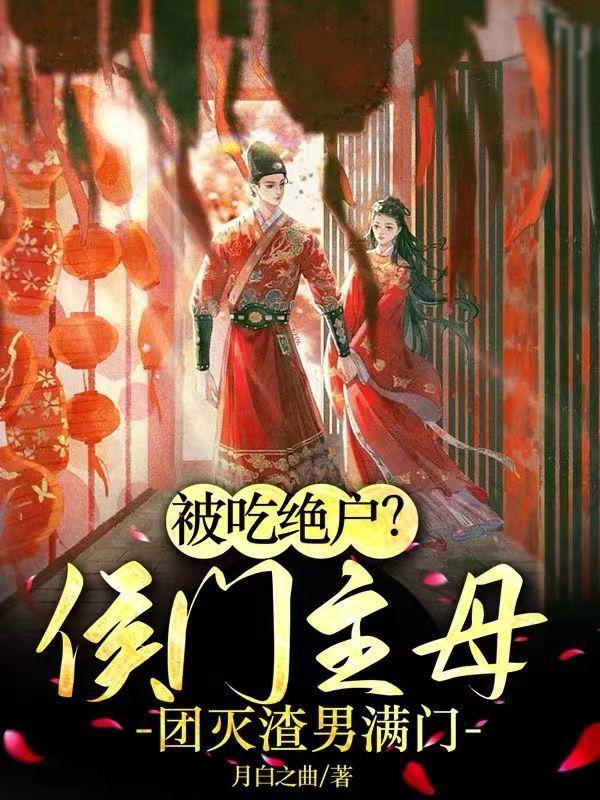书籍简介
首章试读
“傻子怎么一点动静都没了?该不会死了吧?” “死了最好,我们就不用在这鸟不拉屎的外庄待着了。” “那咱们真不管,侯爷怪罪怎么办?” “要管你去管,傻子起疯咬人,我可不救你。何况这么多年过去了,侯爷问都没问过,递去的信也没有回音,怕是早忘记还有这么位正牌夫人……” 大概是回光返照,谢晚云疯癫了半辈子,在生命走尽的最后一刻清醒了。 她躺在冷似铁的被衾里,听着丫鬟的闲话,周围劣炭燃烧产生的黑烟加重了她的咳嗽。 “咳咳……”好不容易止住咳。 外面没声了。 有人推门进来,是个身形伟岸的男人,她的丈夫远兴候,穿着重色的华服,比少时沉稳,也有了白头。 两人因当年宴会上的意外,阴差阳错成了亲。这么多年来,没有相敬如宾,只有相看两厌。 没想到弥留之际,男人会来送她一程。 “咳……”她忍着喉咙的咳嗽,“你来了。” 远兴候看着形如枯槁的妻,心中只有厌恶。 两人年岁相差无多,自己还正值茂年,谢晚云却已老态龙钟,鸡皮鹤,双眼流着浑浊的黄水,头不知多久未梳洗,站得远都能闻到令人作呕的气味,哪里还有当年镇国公嫡女的风采。 “是芸娘叫我来的。”他冷冷道。 谢晚云点点头。 应该想到的。 男人对自己没有一丝情谊,满腔的爱意给了那人。 但年轻时没得到的,老了也不会去奢求,更不会有什么怨怼。 “咳咳……”她又剧烈咳嗽了几声,这次咳出了血。 远兴侯看着咳出的血,嫌弃得眉头皱的能夹死苍蝇,但想到这些年因为娶了谢晚云,在朝堂获得不少谢家旧部的支持,良心尚存,开口道:“你有什么遗愿未了?” 谢晚云的呼吸迟了些,“我是有话想问你。” “你问吧。” “我们的孩子……” 提到孩子,她病骨支离的身子,几乎挣扎地坐起来,“我们的孩子真的死了吗?” 这下远兴候的面上终于波动了,...